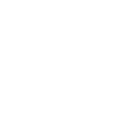“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相辅相成的,”苏黎世大学的语言学家巴尔塔萨尔·比克尔(Balthasar Bickel)说道。他承认,乍一看,这种相关性似乎很奇特。比克尔所领导的全国研究中心(NCCR)演化语言项目,就是致力于研究这两种多样性之间如何产生联系的研究项目之一。
对语言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相似性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自那时以来,多项研究表明,“推动语言多样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环境中物种的多样性”,比克尔说。这种联系最令人信服的原因之一是,当人类置身于更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中时,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这使得他们能够在较小的群体中生存,减少对他人的依赖。反过来,个体社区的形成促进了各自语言的发展。
NCCR的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定居并开始从事农业时,语言多样性与当地生态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当人们还是作为狩猎采集者四处觅食时,他们更加灵活和适应性强。如果当地生态无法提供足够的食物,他们就会迁移到其他地方,以可管理的小团体形式活动,并培养自己的语言,”比克尔解释道。这意味着他们并不一定要与其他(语言)社区合作才能生存。然而,当他们定居并开始种植自己的食物时,情况就不同了。定居使他们严重依赖当地条件,如降雨,并经常受到农作物歉收的影响。因此,与其他(语言)群体进行贸易、物物交换和合作变得至关重要——而这需要一种通用语言。当地生态是否直接影响语言?如果一个像因纽特人这样的民族经常被冰雪环绕,他们是否会为此发展出多个术语?“不,这种现象更多是构建专门词汇的问题,就像猎人或工匠一样,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发展出了特定的术语,”比克尔回答。
事实上,生态与语言之间的联系是间接的。更具体地说,物种丰富的地区允许更多的群体,即使是很小的群体,也能相对独立地生存。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热带雨林——每平方公里的物种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都非常高。而在另一端是贫瘠的西伯利亚。由于在这些纬度下,居民需要巨大的集水区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该地区人口稀少。因此,小定居点群体不得不与其他人合作,以产生足够的生存资源——这使得语言多样性相应较小。
“一个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根据其生态进行预测,”比克尔说。他几年前与苏黎世大学的地理学家罗伯特·魏贝尔(Robert Weibel)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了这一强烈的相关性。
正因为如此,语言多样性最大的地区分布在赤道附近,那里温暖、阳光和雨水充沛的气候促进了生物多样性。事实上,世界上语言最多的国家(839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该国总人口约为900万,分布在约900个民族群体中,每个民族群体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乌得勒支大学进化生物学与环境研究系的一项研究表明,新几内亚也是世界上植物多样性最大的地区。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紧密联系引发了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就像昔日的狩猎采集者一样:跟随巴尔塔萨尔·比克尔的脚步,从一个肥沃的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沿途从生物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这两棵知识之树上采摘成熟的果实。
“我们今天对智人进化所了解的一切表明,人类已经在很早的阶段就努力追求文化多样性,”研究员巴尔塔萨尔·比克尔说。在最早的人类中,可以发现石器工具的形状或使用颜料的差异。很快,史前人类在其他文化表达形式上也实现了多样化,如住房、食物和丧葬仪式。而在某个时候,还有语言。“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早期的智人是否在语言使用上也存在差异,因为我们没有证据,”比克尔说,“但一切都表明,追求多样化的努力一直是人类的一部分。”
这种对多样化的渴望似乎是本能的——而且与语言也有关,比克尔(Bickel)推测道。毕竟,在学习语言时,小孩子不仅仅是在学习语言本身:他们还在学习其母语所特有的世界观、交流规则和价值体系,这些与其他语言是不同的。
现在,不仅生物多样性已经下降了一段时间,而且世界正在经历语言多样性的急剧下降。“全世界语言消亡的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巴尔塔萨尔·比克尔(Balthasar Bickel)说。GlottoScope网站指出,在全球总共7737种语言中,近三分之二面临灭绝威胁或不再传承。欧亚大陆尤其受到影响——但还有澳大利亚南部和北美,那里对土著文化的蓄意破坏导致了许多土著语言的灭绝。
一个社区失去自己的语言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比克尔说,当一个群体失去自己的语言时,它就失去了很大一部分身份认同、对某个地方的归属感以及与同龄人的熟悉感。“社区语言的丧失有可能造成巨大的社会和心理损害,”这位语言学家继续说道,“因为语言是人类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幸运的是,语言仍在不断多样化,”比克尔补充道。他以全球语言英语为例:苏格兰英语、澳大利亚英语、美国英语、南非英语、印度英语——它们之间在发音上都有明显的不同,并表明说话者属于哪个全球语言群体。即使英语像入侵植物一样传播,比克尔认为,人们仍然有区分不同英语版本的冲动。“没有人能抗拒这种冲动。”
但回到语言灭绝的严峻状态。这与生物物种的灭绝有相似之处吗?植物和动物物种正在消亡,因为它们的自然栖息地正在被人类破坏。在世界各地,我们正在改变自然环境,清理和人口稠密化土地,种植和施肥作物,修建道路。而且,随着小规模农业被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所取代,更多的物种面临风险。
大型主导语言是否像单一作物对生物多样性那样对语言多样性有害?世界语言是否应该为少数民族语言的消亡承担部分责任?一种语言是否因其新使用者的数量众多而得以立足?随着世界语言的传播,它们是否正在排挤地方语言?“不,”比克尔引用了一项关于这一话题的全球研究来回答:“语言生存的最重要因素是学校教育。”这是因为教育主要通过语言进行,而语言是基础性的:没有它,一系列不同的人类特质和成就根本不会发展,尤其是个人身份的意识。
现在,在大多数国家,学校教授的国家语言与社区的日常语言并不相同。比克尔认为,这种“高级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当地语言的声望。但为什么瑞士德语、加泰罗尼亚语、诺曼语、北弗里斯兰语、南萨米语以及许多其他当地语言仍然蓬勃发展而没有消亡呢?“要让一种地方语言保持活力,似乎只要每个人在课外时间都能自由地使用它就足够了。只有当教师、学生以及学生之间只用国家语言交流时,地方语言才会消失,”比克尔解释道。
只要人们思考和交谈时自然而然使用的语言是当地语言,它就会占据主导地位,而国语则排在第一位的外语之后。然而,为了说明国语如何能够成功取代当地语言,比克尔提到了尼泊尔,一个进行过大量政治和语言研究的国家。在皇权统治时期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国范围内对当地语言的禁令都失败了——尽管人们在市场上说当地语言时会被殴打和逮捕,但通过法令实施国语的尝试也失败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尼泊尔经济发展兴起,当地语言才开始承受压力:此时,只有国语尼泊尔语在学校和媒体中使用——并且正在开发通往偏远地区的通道。“导致语言消失的首要因素是道路建设,”巴尔塔萨尔·比克尔说。如果一个偏远地区(岛屿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的居民说一种少数语言,并且该地区通过公路或铁路与其他地区相连,那么当地语言社区将受到根本性的影响——正如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尼泊尔就是这种情况,那里的偏远地区以当地语言为主,并与全国公路网相连。结果,尼泊尔的语言多样性急剧下降。
另一个例子是格劳宾登州的山区,那里的人们说着罗曼什语家族的语言。19世纪,该地区交通变得便利,从而催生了旅游业。因此,用罗曼什语交流的价值贬值了。就连当时的当地人也意识到了其他人都不会说的语言所造成的经济障碍,并最终同意在学校、教堂和政府办公室改用德语。据Lia Rumantscha网站介绍,只有在罗曼什语有彻底消亡的危险时,才采取了行动:1982年,苏黎世大学罗曼什语学者海因里希·施密特创造了罗曼什语格里什恩语作为官方标准化的罗曼什语,1995年恢复了罗曼什语在学校、行政和公共生活中的使用。然而,罗曼什语灭绝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罗曼什语地区的学校仍面临在保护当地罗曼什语和适应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等强势语言之间找到适当平衡的挑战。
随着新道路的出现,不仅仅是外国游客到来。迟早——无论是否故意——外国植物和动物也会被带入,这些物种往往是侵略性的,可能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潜在的破坏性影响。一旦一个多样化的系统受到损害,通过人为干预恢复平衡既耗时又具有挑战性——这一事实对于语言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同样适用。